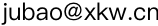专栏介绍:学科网百万级别新媒体加持,期待您的分享!(👉投稿方式请见文末)
温馨提示:投稿文章为老师原创作品,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摘要: 乡下人被称为土头土脑,在我的东北老家,乡下人叫农老卡,意思是卡乎乎的,近乎猥琐,有骂人嘲讽之深意,说话者大抵是城里人,大有唯恐被沾染上病毒似的。乡下人被叫做农老卡,源于经济上穷困,土里刨食的挣钱方式,他们拿钱很金贵,消费又极节俭,就地取材者居多,能省则省,夜间能不点灯就不点灯;岳母家的电视早已经不看了,岳母说看了眼睛累,实则怕花钱,怕平时不积小,到家里有大事的时,拿钱费劲。
关键词: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
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本色》一文中写道:“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我认同这句话。在农村呆的时间长了,和外界就几乎是隔绝了,即使他们年轻时曾闯荡过社会,是个社会人。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他们分别在四五岁从城里来到农村马家屯,一个从金州城,一个从沈阳。妈妈还在未婚前到哈尔滨服侍过大姨做月子,还生动形象地对我们兄弟讲过路过鞍山,是在晚上,在火车上,往窗外一望,烟囱冒着熊熊火烟,这烟火来自于鞍山钢铁厂,可他们到了中年,我们几个兄弟在家乡教书、在商场销售或在家务农,妈妈总会安排我们到村外办事,她在家中、东园的地里、西园的地里、山顶的荒地,筹划着一切,安排着种庄稼的茬口,像个女汉子一样,和父亲天天到“地里”上班。妈妈的能力也不差,她被土地拴住了,她边干着活边寻思着儿子们的事,掂量着人来人往的陈年往事。她即使很累,看到儿子一家三口归来,也会喜笑颜开,动作麻利地从地里抽出稼杆归拢到一处,拾抱到大棚墙边。
费孝通老先生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我的父亲也曾说过:“人这一生,吃土,穿土,用土,最后归于泥土。”细思极“信”,世间的食物、丝绵、木头、瓦片等都来自于大地,人死后,还要觅一块地,作坟堆。我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工作于乡土多年,我没有“父业子承”,我不会种地,可我相信土地的神奇,我自诩我的最大特长是种地,终无明证的了。
“土地”这位最接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费孝通老先生如是写道。“土地”如母亲赐予生民生存、生活、生育所需的一切,她是农人唯一的生活来源,没有了土地,大部分农人将啥也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了解这一点:生活在中国基层的农民很惨,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没有自强自立的信心,更多的是哀声叹气,迷信命运,他们不像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有工资有津贴补助,有奖金,只有土地才是他们施展才华、傲霜沐雨的舞台;只有将汗水洒在土地上,任劳任怨地干,春耕夏耘秋收冬储,老天爷帮忙给力,夏天地潮湿,天不干,付出也许会有收获。将土地的农产品销售出去,也是极不容易开心的事。菜贱伤农的事屡见不鲜,货到地头死更等同于路毙农人了。像在北方或南方,西部或中部某些城市区域那里的工人工资低,在父母的时代,马云、马化腾之流家喻户晓前,周边的农人更苦了,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不会高,物流亦不畅通给力。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听闻过同事周说,他们江西农村附近的几个村落都是周姓,其他姓根本打不进来。即使有外姓进来,也会被孤立,被搞走。我几年前也听自己的大舅哥说过河北的乡村有的一个村子的男的都打光棍,一辈子不找老婆。这些光棍,土地就是他们的母亲,就是他们的梦中情人,让他们挂着的是一年四易的生活元素,春天他们看到了希望和前景;夏天他们看到了忙碌的征兆和庄稼的生机;秋天他们看到了辛苦付出后苍天大地的赐予,无他来源,祈祷人生的平安;冬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身影,默享着独处少消费的时光,咀嚼着岁月的口粮。
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中写道:“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在此文中,他又写道:“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周边地上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我之理解“拖泥带水”用得极为精当,农人何啥都不想“鲜衣怒马”?自身条件不允许,客观环境也不允许,早晨未晞的露水,黄昏起的露水,雨季泥泞的阡陌和沟渠,沾湿了农人的布鞋、水靴、裤脚、袖口。此处污泥浊水的处境,保持光洁的行装很难得,干活越下力的农人浑身便像是在湿草地上打滚后爬起来的一样,你分不清他身上哪儿是汗水,哪儿是雨水,最惬意的莫过于觅到一处清灵灵绿草柔柔的水渠沟湾,先弯下腰,洗净劳作后的土一样颜色的双手,或索性掬一捧水清一清布满汗渍的颜面,一次不过瘾,大可再来一次、两次。驻足水中,鞋窠里满是水,双脚晃动,荡起水波,微觉窠内有沙砾,农人又麻利地脱下“宝鞋”,净洗尽力甩开,双足雪白,踩在硬硬的石板上,着上贴己的鞋走开了,农人走过的、停留的地方又恢复了大自然的原初样貌。费孝通说一个“讨”字道破了农人对土地的虔诚,对土地神的崇敬。我家在官道西有一块地,我们叫它西园子。初始为南北向,后几家插伙,改为东西向。父母服侍土地勤恳舍得出力,三百六十五天无歇日;干好了夏天的菜蔬,就干冬天的暖棚,四季收入不多,却保持不长时间间断。这里种过芸豆、地瓜、韭菜、丝瓜,后来果木代替了菜类、豆类、瓜类。西园种了樱桃树、桃子树,也许是土质沙性不含水,樱桃树没有长好,桃子树成了父母收入的主要来源。桃子树在夏天炎热的时要打杀菌药、杀虫药和保护叶面的水肥等。父母不舍得花钱,也不懂电动技术,就靠着人力笨办法,母亲拿着打药的长长的管子的一头出没在桃树的枝叶、树杈中,身体不断地升降,面部也不带着口罩,冲天的雾气在母亲身后经过的地带。父亲在园子的另一头,双手推压着铁杆,挤压泵里的药汁流向长长的管子的另一头。父母的辛苦劳作让我认同费孝通先生表述乡土生活时用的“讨”字。一次,父母在西园种菜,园中的泥土早已如同净抹过一样无杂草无杂石。天微温,日欲斜,邻村放水的何老五伛偻着腰,蹲在水道沟的沟帮上,看我们父母“攒菜”(当地话的意思是刨坑下种)。他就压低了声音,用粗嗓子说:“福勤、宝香,你看看,就不希干了(不用干了),斜坡上的地就让他荒了又能怎么地了?”父母只是笑笑,无语以答。这种种地的精神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是美德,是值得表彰弘扬的,而乡下人有的把“不当回事”视为洒脱大方,实际上是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在作祟,把种地当作耻辱,把坐在办公室当作体面的事,这就是他们的中国梦。
乡土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如是做论断。乡下人喜欢说东家里长,西家里短的。喜欢议论谁家的婆媳关系不好。喜欢评说谁家发了大财,谁家的儿子有出息,赚了不少钱。喜欢说谁家的媳妇漂亮招风,喜欢说谁家的孩子念书好,考上了xx大学,内心异常羡慕,外化为啧啧称赞声。乡下人彼此见面,按礼来说,是要打招呼的。关系不错的,会停下彼此的脚步,聊上几句,温暖彼此的心,相互心灵拥抱取暖,却并无实质的问题的探讨,只因那世交的关系。农村有红白喜事,自有农村的办事规矩。大管事是村里的人,帮忙的也是村里的人,挖圹的是村里的人。办事的费用趋向于比市场的价格低,一则是真心真意真出力应该有此费用;一则是彼此很熟,邻里邻居的,从道义上讲应该“义”字占一半。村子大什么人都有,村子里有大厨掌勺,炉火一生,大锅一开,四五十桌酒席不成问题,地点就在自家宅基地的房前屋后,桌椅自设,碗盘碟在镇上是有专门租售的。男主外,女主内,里里外外,热热闹闹,人气很盛,办喜事的人家常被调侃,祝酒辞之简洁“大家吃好喝好哈——”。办白事的人家村里人也会随份子,多少随人随情,差距不甚大,专门有人收“款”记账,年龄相近或相同的一辈人会陪着主人坐坐,在时光的沉寂中,无语是最高的同情、祈祷,主人的哀号自会有关系不错的人劝导、抚慰。母亲去世在2017年正月十四,出殡日正月十六,当母亲的尸体入棺,被乡人抬走时,我们晚辈的痛彻肺腑,百身莫赎。父亲坐在里间的炕上大号哀叫,自有乡人左劝右劝的,“想开点!”“还有孩子!”
乡下社会是熟悉人的社会,弊端也是有的,容易有红眼病。看你家发财了,心理不平衡,“气鼓愤”。看你家过好了,不向人家学习借鉴,对人家冷漠。家乡的山地梯田是计划经济生产队时代的产物。现今年老,当年年轻的社员学大寨,荒山变大田,庄稼盈山,野草仅余沟畔路边。进入农村单干的年份,一些农人责任心不强,干劲不足,天不帮忙,梯田荒芜,收成几无。年轻的一代想租买梯田,年老的内有戒心,以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肯租卖,或出高价,或出尔反尔,不讲信誉由此得出了如下的说法:在农村,在买卖上不好办事,就是彼此太熟了,买方赚了,卖方觉得吃亏了,被骗了,被算计了,买方赔了,卖方此许会觉得不好意思。在我农村老家有如下的例子,一房地产老板买了农民的大田盖房子,农民得了不少钱,揣在自己的腰包里高高兴兴的,可是房地产老板倒霉透顶,因为建楼地址距离军事基地的火药库近被联席会议否决了建楼租售的方案。老板这下赔大了,老板的老婆和乡里人都是熟人,就说:“你们少出点钱,把地买回去也行。这样赔了,我们也乐意。”可村民们无动于衷,把兜里的钱捂得更紧,想把钱从我这儿弄走,门都没有。农民挣钱难,积资更难,乡下人彼此办个事既有讲究的,也看是否投缘,二人有仇有底火,别说有生意,竟是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熟人社会彼此交往,利益考量见感情,也见乡下人的心性、眼界,讲究多,心却狭隘,属于犁二弯子朝一面翻浮。
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费孝通这样总结到,他通过文化源泉来讲。我觉得城乡对比更好理解一点,我家亲戚是住在城里,且不说是在北方哪个大城市,到了我们家很会说,很会演戏。“大舅,大红、二红如果考上大学了,我供他们。”说时,毫无顾忌。还真的是我们到了亲戚所在的城市里读书。他只弱弱地和儿子谈了此事,竟无下文。其实,我们不计较诺言兑现与否,倒是觉得城里人明知道乡下人的苦与无奈、累与无功,却愿意说那些撩人的漂亮话,打出亲情牌、高大上的旗子,自己却节俭如农民。这是城里人和农村人的不同,源于站位不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一楼只能看到草皮,三楼能看到游泳池,二十七楼的能看到港珠澳大桥。”也真怪有其母必有其女。前些年,母亲还在的时候,大姐来我家,能说会道,大侃特侃。临走时,撩上了离婚内卷化的大弟:“缺钱跟大姐说啊,别怕!”转身出门,走天涯了。此行来我家,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掉,我的一家人全程操办销费。只是京城来的大姨给我妈甩了一千块钱,算是表达了他们归乡祭老的诚意了。还有位亲戚来自北国的省会城市,来到我们乡村,落住山顶新房,住了两年左右,临走时,连酱油瓶里的一滴酱油都没剩,惜物之程度令人“惊为天人”。亲戚的后老伴实在看不上眼了,在我母亲过生日那天,强行让亲戚给了我妈二百元钱贺喜。这位亲戚大人每次上村北的集市见过我母亲就会说:“宝香,需要什么东西,我帮你捎着。”其实,人在江湖混,何须此虚言。城里人嘴好,这是乡下人的一个总结,从人际交往上来看,就是太虚了。他们或在毛泽东时代,熟读成诵“老三篇”和语录,难道不记得《论人民内部十大关系》中提及的名声与利益相一致的关系嘛?只是习惯了动嘴,惹得乡下人怪厌恶的。
身在农村,讲大道理,乡下人不愿意。他们会说你“吃着地沟油,操着中南海的心”。身在农村,讲小道理,接地气的东西,属于点醒的范畴,还是大有市场的。这小道理有自老一辈得出的处世经验,如“路边的野花,你莫要采。”“一张小嘴能把人吃穷。”“五更早起开大门,金银财宝进家来。”“男人出门,带着女人一双手。”“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养儿防老。”在乡土社会,怕就怕思想愚昧却把孩子管得死死的村民。“屋脊开大门,万事不求人。”满嘴都是怨言,浑身都是戾气,“啥事都是爹妈的错,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老的,就是偏向。”“不用劝,你们不知道这里面的事。”
在乡土社会,农人对彼此熟悉,对“物”也熟悉。“风在雨前头,屁在屎前头。”母亲边干活边戏谑道。“七七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黄牛遍地走。”“羊有跪乳之恩。”“羊这个东西,发贱,它不喜欢吃的东西,饿死它,它也不吃,宁肯吃鞋底子。”“马饮干净的水,牛喝脏浊的水。”“狗没有肝,牛没有上牙。”交配期的狗,“和谁好都是指定的,其余的狗都是起哄的。”小燕子低飞啄虫,长虫(蛇)过道,天要下雨了。“黄瓜是最解馋的了,缺了水,少了肥料,它是长不直的,净弯弯的。”瓜蔓摆放南北向,朝东的瓜结得大。“老驴老马忘不了家乡。”“草盛豆苗稀”,植物的生长也有侵略性。颜值周正的苹果未必甘甜好吃,带疤不对称的苹果更好吃。农人和他们的子弟分辨麦子和韭菜很容易,状、色一样,但麦子扁、硬如一张纸,韭菜厚、嫩如葱水灵。这麦子的生长也特奇葩。冬天踩踏小麦,惊蛰后,它长得极有生命力。为了春季的小麦长得好,不缺苗,生产队还派社员专门到麦地里拉石滚子,碾压霜打期弱势的一丛丛麦子。苦麻菜带乳汁,人吃了去火。
农家的孩子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干于家土,拔猪草、割牲口草是他们常态的活。春来菜长,夏雨过后,农家子弟着棉槐条编的筐,拿着父辈给定制的刀,串沟走垄,去山上,拔菜了。他们风卷残云,有用的猪能吃的菜,都被他们切根割叶放在筐中。他们有时运气好,菜拔得多,他们的归途是漫长而劳苦的,可他们不愿意放弃。小小的身躯弯弯斜斜的,一手挎着筐,胳膊肘被重重一筐菜的筐栏勒出一道道红白相间的印痕,他们有说有笑地走着,也看着同伴使出浑身力气调整姿势,往家的方向移去。这是乡土社会农家孩子的身影,相较于城里的孩子,他们真的是“天人合一”,他们熟悉大自然社会,少谙世态炎凉,他们不是很擅长“形而上”的东西,却往往能把乡土中的技术活做好。拔菜还用人教,简直是笑料。他们大多有着大地一样朴实无华的品质,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方法——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刚入沈阳读师范,大四的大高个操着辽西口音的师兄说:“你很老实,你会被人欺负的。”他所说的老实,就是我不太爱说话,不爱惹事,不喜欢向人家提前输入自己的“真经”,不擅长研究对方的心理,愿意以独善其身的方式去处理周遭人际的关系。“大爱无言,大德无语,大才不争。”这也只是传统文化表达时言未尽意的一面,话语自有道理,但是是有前提条件的,是盲人摸象中象的身体的一局了。我感激成长中遇到的一切的人,他们曾帮助过我的,但我的成长确实打下来很深的乡土烙印,少心机直性无算计,“把活儿干好就得了,想那么多干什么。”“瞎操心干什么。”“你把书读好就行了,家里的事不用你管。”在我的乡土成长青春期,遇到过家族叔叔抢房子、抢接班的事,但我们心中有话却没能表达出来,我们本应把事理捋顺,却因为长辈窝囊不善言辞,不能把话及时说开,造成了各个人心中的影子,家族人际关系内卷化就这样了。不把理说开,没有强势的长辈,在乡土社会中成长的孩子在面对多个长一辈的,是表面不关己事,内心是着实痛苦,因为自己的长辈也受到牵连,彼此心里都有着阴影。却又不能在说什么大道理。乡土社会遇到一个混账媳妇,加一个软皮蛋的长辈,这个大家庭若想和谐,那等同于白日说梦。
费孝通说道,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的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格来应付的。下面我谈谈自己的切中感受。社会如此,被时代裹挟的个人亦此。我是在八九、九〇年两次向高考发起个人最强有的冲击。我用金了自己的力气,焚膏继晷地学,那时乡间晚上停电是常态,我们兄弟俩熬夜点蜡学,学到深更半夜十二点余从小厦“书房”里下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成长中,与大人们我们寡言,与老师内心早有评议,只是不愿意和他们交流,或聊聊天,或近乎插科打诨的。个人满脑子都是应试的科目、无休止的作业音符,人际关系也是考虑的,除了体育我强势外,其余则不愿抛头露面的。考上大学,在师范学院呆了四年,这四年变化是有的,但你冲洗不净这乡土社会的烙印的。一间宿舍八个人,有来自城市的,有来自镇上的,有来自农村的。从为人处事方式来看,来自于城里的善于交际,人也长得白白的,观之有味,闻之有趣,审之有家庭背景,业余爱好多,会下棋、打麻将,会和女生来往互动等。来自于农村的,他们拿手的是苦学不辍,甘于刷题,不问东西,不问收获。在宿舍里,人际交往中处于劣势,话语权不多。爱好不多,交际少。不善“逢场作戏”,习惯于被人摆布,倒是胆小怕事,不愿争辩。不缺钱花,平安无事,便是人间乐事了。同学间有借钱的事,一般是乡村跟乡村来的借,逢借必还,承传了乡村社会讲信誉,“用人格办事,用成绩说话”。乡村来的男生无疑乡土社会的凤凰男,可到了城里来读书,毕竟父辈们欠债太多,城乡差距大,“没有甩头的”居多,办事不干净利索。这些靠读书应试上大学的男生常常暗羡省城的女生,他们不会暗送秋波,不会甜言蜜语,只好乡村式给对方送些更好的果品——北国鲜见的香蕉等。城里的女孩子见“此等把戏”早一眼看穿,把乡村男孩当作一个犯错误的男孩子去审“你怎么能这样?”“我觉得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言外之意,你是农村的,又穷又无社会背景,办事能力不强,死也不会跟你这样阶层的人搞到一处,别做梦了。)“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谢谢了。”来自镇上的师范生,他们的处境居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庆幸的心理,有遗憾的阴影。作为应试上大学的师范生,其难度自有区别,有省属、市属之别,有城乡之别。在那个时代,乡村的孩子上大学的分数高于省城的30分之多,所以乡村的孩子上了大学,他遭受应试双刃剑的负面更重些,纯粹的“傻闷嫩”了。搞娱乐活动,农村来的张不开嘴,他们不是不想唱,他们不会唱,他们压根儿没听过、没学过,他们中学的应试生活就是他们的一切了。可乡村来的师范生他们也不笨,在热心的城镇师范生带领下,慢慢融入班级小集体当中,也会哼唱几句“两只老虎……”,虽然不连贯,虽然和乡村社会无甚联系,乡村若有老虎,人都会被老虎吃光了,老虎哪有闲空儿和你玩,城镇居民的人闲暇时光多,唱歌调情是主要的,哪管内容的真实性。一次,李天骄跟我说:“你们跳舞怎么不穿皮鞋,穿踢足球的鞋。”当时,我听了很诧异。过了多年,在城中生活了若许年,我理解了。跳舞是很社会化的事,是交际的基本仪式,是讲品味档次的。其中跳舞最欢的几个乡村生李天伟(不知道现在改名没?)和我等,哪知道这些,只知道班级有活动,要参加,不能搞不合群的事,谁能想到90年代初这跳舞稀罕物的种种讲究,没有考虑到城中女孩子的具体感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乡村孩子读大学没有拉帮结伙的事,倒是城里来的孩子更世故些,喜欢拉帮结伙对付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系里谋个“官差”,在同学面前施展口才,为毕业后的就业“添光加彩”。这无可厚非,这活儿也只有这些人张罗,去搞得红红火火,让本系名声大噪,让其他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赢得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喜气。在与人交往中,乡村来的学生“慢热”,谈吐气质“土气”,他们本人也知道,这种“气”要靠时间来消散。几年前,刘兆伟教授来珠海参加学术活动说过:“有个学生说,到大学,啥也没学。他是这么说,可是读了几年,气质改变了许多。”乡村来的孩子与人交往热心实在如泥土,他们少会说“不”,这就像泥土不拒绝一粒种子,终让它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可乡村的孩子少见城市里的复杂事件,热心肠办砸了事,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住在一个屋檐下,哪有不磕磕碰碰的。来自城里的中下阶层父母少文化素质经济颠簸不定的,有流氓习气的男生喜欢动手,和男生打架斗嘴是不少的事。在大学我遇到的这样的男生叫李太茂,打架挺讨厌他的,喜好抽烟讲艳遇。这小子个高,脸皮厚,在正规杂志上发了篇恋爱史,系里搁不下他,走路喜欢晃,额前发长过眉,眯着眼看人,自觉甚美,他欺负城里的肖大勇,肖大勇圆滑处之,刚柔并济;他欺负任文涛,任文涛这个来自辽西的,就闷声不响的,李太茂的声音就越发大些。我来自与辽南农村,我内向多于外向,我自觉善于交际,我临场发挥欠于事后权衡,我与辽宁东李太茂的交往,他处于上势,我处于绝不妥协之势。他抢我的水杯用,我不和他计较;他说我的球踢得不好,我不反唇相讥。他见我在课室努力练书法,安静读书,嗤之以鼻,哂笑复哂笑。我和他“冷战”到底。他说我球踢得好,我一笑了之。说实在的,我和他不在一个频道上,他有时看我不顺眼,就说了;我有时看他不顺眼,就转身他去,无语离开。城乡人汇集在陌生化的大学或学院里,乡村来的感到了极度的不适应。这水土不服,从理性上看,是生活环境改变了,改变的成分太多,省城人心理优势一第一于全省的和超越的,乡城人找不到存在感,想刷存在感几乎无市场,只好在有限的几个平台争雄斗狠了。现实中,一省之地域之巨大差异,城乡之天壤之别,乡村人回归农村中国社会最广阔的基层,内心有石头落地的踏实感,但在精神层面的落漠却是要带入泥土的了,活着彼此见面,畅谈后辈,后继有人,但言及当下的处境,农村永远不发达,不入时的代名词。若历史可以重来,家境殷富,天赋尚可,父母职业光鲜,在此环境中,行走在师范院校, 我自可雄心万丈有事说事,办事有路,我哪还会有压抑。但历史不会重来,我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熟悉于乡土,我在远方的城市只有适应、跟着走,学习如此,学术如此,胆小有时如“鼠”,肖大勇跟我说:“GH,你太老实了。”我何尝是老实,我背负着乡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的流弊,我苦脱于这个熟人社会,学会冷漠,学会习惯孤独,学会于在不同场合表现自己,聚会时不再低着头,闷头造,不管他人眼神和所想,饿着也要表现自己的风度和谈吐,习惯于别人的表面热情而内心的势利,习惯于人走茶凉、过眼云烟的都市流浪,人过中年,常忆旧时阶层、环境之烙印,品味当下众生相、南北东西文化大餐,乡土社会还是个人美好而无奈的社会,它有故事,它有苍凉,它有传承,它又与时俱进,充满着活力。
文末小贴士
01作者介绍
高山,现任教于珠海市第二中学,曾任教于大连市一〇二中学语文教师。2009年被授予珠海市先进教师;2012.9 在珠海被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共广东省教育工作委员会授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2023年在珠海被珠海市教育局授予“珠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02投稿通道
教师频道面向一线教师,全面招募原创稿件,稿件一经采用将有电子证书及实物礼品奖励。投稿请扫描二维码加入群聊,与全国各地教师共同交流。